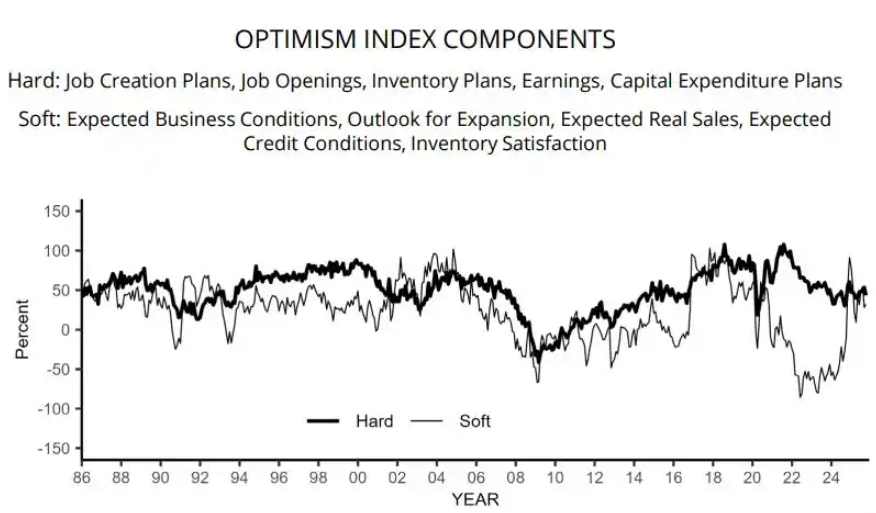导演马岩谈话剧《恒星》创作:通过喜剧反观普通人生活
(字幕)话剧《恒星》名称的由来?(同期)马岩:因为自闭症人群有个说法叫“来自星星的孩子”,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行为方式,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后来我们也想了好多这样的名字,后来还选择这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行星上,太阳是恒星,很炽热,会发光,它会闪耀自己也会照耀到别人,这种东西是我们想从题目中表达的。这也是我们做这部戏的目的吧,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现在压力都大,不管有钱没钱,生活好次都有压力,但有时生活中的小动作,可能你的一句话就改变了一个人,可能别人的一句话鼓励了你,你这个坎就过去了,没
【摘要】 (同期)马岩:因为自闭症人群有个说法叫“来自星星的孩子”,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行为方式,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后来我们也想了好多这样的名字,后来还选择这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行星上,太阳是恒星,很炽热,会发光,它会闪耀自己也会照耀到别人,这种东西是我们想从题目中表达的。
(字幕)话剧《恒星》名称的由来?(同期)马岩:因为自闭症人群有个说法叫“来自星星的孩子”,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行为方式,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后来我们也想了好多这样的名字,后来还选择这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行星上,太阳是恒星,很炽热,会发光,它会闪耀自己也会照耀到别人,这种东西是我们想从题目中表达的。这也是我们做这部戏的目的吧,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现在压力都大,不管有钱没钱,生活好次都有压力,但有时生活中的小动作,可能你的一句话就改变了一个人,可能别人的一句话鼓励了你,你这个坎就过去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尤其是看话剧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其实有更多的问题,但反而社会更需要这些年轻人的力量,那我们做点年轻人的戏,有人做了喜剧,有人做了先锋艺术,有人做了当代艺术,有人做了经典的重排,那我们做一些说老百姓的故事,可能不代表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看完之后说,我以后做事情,见这种人可能我换一种心态更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就够了。不管这个故事大家看了在虐心,或者看了是讲自闭症的啊,我们觉得其实都是讲自己的故事,讲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的故事。(字幕)真实的自闭症家庭是怎样的?(同期)马岩:其实从写实上面来讲,自闭症家庭的孩子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往往作为兄弟姐妹是疏于被父母照顾的,因为孩子有病要去治,尤其是自闭症,有些孩子需要四处奔走去治疗,而且要24小时陪护,那么两个人中小的那个,童年中就会失去些东西。这也是我在实际接触中,有一个家庭也是这样的。他们有感觉也有互动,只是我们可能不了解他,不了解他的那套体系,可能跟你打招呼是摸你耳朵,有人可能会觉得你没事碰我干什么,正常人可能会觉得不适应,在他们这可能摸一下耳朵啊,或者击掌这就是打招呼。(字幕)如何与自闭症病人相处?(同期)马岩:其实就是磨合,我们做戏,艺术嘛真善美,真就是真实,其实在真正过程当中,就是两个人意见不合,或者亲人、爱人、朋友之间,哪怕同事、陌生人之间,有意见的不合可能会争吵,会争执,甚至会冲突,但是就因为这种冲突与争吵、对抗,才有火花,有各种有样的故事,比如说像恒星里面哥哥对于整理书籍对于家里的摆设都是都是不能变得一成不变的,但是妹妹过来之后因为要布置一个简单的灵堂,要收拾母亲的东西,这样就引来哥哥的一些不能说不满吧,就是打破了他自己的一个规律,所以两个人在这方面起了一些冲突啊,包括争执啊,包括一些冲突,对抗,比较有意思。(字幕)剧中有趣的点如何形成?(同期)马岩:我们从处理方法上,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我们看一个自闭症患者或者是看一个所谓的有些人,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接触他们都是通过一些义工啊,或者这种公益的活动接触他们,但如果把他们客观的放在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其实有些事情会让人觉得比较有意思。而这种有意思不是刻意的搞笑,而是真的跟我们正常人之间的一些差异,不能说正常人吧,就是跟我们其他人的一些差异,会让我们觉得有意思。而且我们正常人的话,我们每个人,普通人也有所不同,各种性格啊,各种各种的生活中一些脾气秉性都不一样,所以再加上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特殊人群,所谓的这种孤独症的人在一起的话他肯定会比较有意思,因为他们属于自说自话,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跟行为体系,而我们正常会有这样的,比如说他可能,你叫他名字,你说“马岩”“你好你好”这是我们正常人的这种打招呼方式,他们说“郭斌”“谁啊”、”是谁“或者说”郭斌是我”就是这种简单的台词或者反应。就跟我们说的正常情境下的表现不太一样。(字幕)创作初衷?(同期)马岩:其实我们做这个戏的初衷,当然啦,我们可能也是要关爱这部分群体,也要去进行理解,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创作角度出发,我们还是想把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而引发我们正常人对于我们生活的思考。就像好多看过的观众就说这戏不太像是说真正的公益啊,或者让我们关爱这部分人群,了解啊,觉得好像是,有时候他们看着主人公郭斌的一些行为,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跟他也一样,我的作品,我后来反观自己的好多作品好像都是这样,就每个人物,可能原来创作的时候都有每个人的性格,有一个特殊的性格,而那个性格呢,观众一看,噢,这跟我生活中的谁谁一样,或者就跟我自己一样,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细节放大,从生活中提取出这个人的细节放大,比如就像是郭斌,他可能有整理癖,他要把书按照拼音字母表的顺序,然后按照英文字母表的顺序,汉语拼音的读音给分类整理,然后他的衣服所有都是一个颜色,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生活状态的周围人都有,都有这种状态,然后他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是自闭症,自闭症都这样,但实际上我们把一个点抠出来之后会发现,其实我们也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在某个状态里面也是生活成这个样子,其实就看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喜剧创作角度出发,我们还是用了这种方式,就是把生活中的一些人物的细节逐渐地放大,一直放大到一种我们说在舞台上的病态,一种病态的呈现,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觉得更有力量,而且大家接受起来,我个人觉得会更容易,就不会太费脑子看这个戏,可能看着看着,刚开始可能还觉得这个自闭症还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人是这样生活的,但是慢慢看着看着,看到第三幕第四幕或者中后段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行为可能我自己平时也有,我平时也是这样的。(字幕)为何会选择自闭症题材?(同期)马岩:像《恒星》这部作品,我们之所以选择这种题材,把主人公设定为自闭症患者,故事发生在一个自闭症家庭的家长走了之后,只剩下兄妹俩这样一个设定,其实真正意义在于每个观众心里想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主观创作角度来讲,我们这么做,一是题材我们好把控,二是可能会更有意思,会有更多故事出来,而真正有意义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好好讲一个人间喜剧这样的故事,让大家看完这个喜剧之后,能反观生活啊,或者开车时候刷点路怒症啊,或者坐地铁不会因人多而烦啊,可能会是这样,反正我们做戏都是秉承这样一个目的,大家看完之后哈哈一笑,回去之后更好的生活。(字幕)被外界喻为中国版《雨人》?(同期)马岩:其实我也看了《雨人》这部电影,从结构上来讲,包括从主人公关系上讲是一样的,其实有些相似,《雨人》讲的是兄弟之情,自我救赎的过程。而《恒星》稍微不太一样,虽然也发生在上一辈人的母亲去世之后,兄妹俩从不理解到理解这样的过程,可能没有自我救赎那么沉重,反而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其实就是自闭症患者跟一个正常人的妹妹两个人生活的简单故事,但是他们之间的碰撞会有一些跟《雨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中新网路伟北京报道![]()